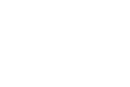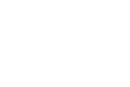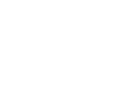1946年5月,臧克家偕夫人郑曼从重庆去上海开展作业,直至1948年末,他们在民盟安排下去香港,前后在上海共待了近三年时间,这算得上诗人的一段光芒韶光,一反抗战八年他在大后方的消沉。首要,他的诗词大受上海市民欢迎,他也生平第一次正式被敬称为“诗人”。
再则,他到上海不久获悉恩师闻一多在昆明被暗算,他立誓要像恩师那样“义愤填膺,以笔为枪,向漆黑的旧实力开战”。正好那时上海武训校园校长李士钊约请他来校教学“诗词创造”课,他就以讲堂和上海文汇报为渠道,宣传恩师和他自己的诗词著作,并告知公民新诗有必要变革。
诗人在上海这三年,应该说是他毕生难忘的年月。但令人困惑的是,在现有资猜中,包含诗人列传、自传和年谱,都对这一段史实或语焉不详,或避而不谈,有似诗人前史上的一段空白。
其原因我的教师李士钊生前曾有解读。他以为1951年的“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运动”后,当年武训校园有些师生为了避嫌,不肯和“武训”有任何纠葛。跟着年月流逝,诗人这段阅历逐步被人们忘记。但前史不能总缺席。当年我曾是臧教师的学生,是亲身耳闻目睹者。现在我首要参阅当年的报纸杂志,尽力回想教师在这段韶光中的轶事。
臧克家当年从重庆到上海挺费周折。1943年4月至1945年秋,他在重庆的仅有作业是赈济委员会专员,并兼《难童教育》杂志主编,所以1946年4月,他只能以夫人郑曼所在单位“中心卫生试验院”眷属的名义去南京“复员”。其时由试验院包了一艘“成功号”轮船的拖轮,整体职工在拖轮上通过20多天长江水运的波动,才好不容易抵达南京。
臧本预备在南京稍事歇息后就去上海,恰巧一天在南京国立编译馆遇到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季羡林。臧和季虽是山东省一师的同学,但不是同一班,臧要比季早好几届,因而在南京是他俩第一次相遇。不久臧先去上海,应聘《侨声报》副刊主编,住在该报在虹口东宝兴路138号职工宿舍。季则带着五六大箱书随后抵达上海,和臧一同暂住在这职工宿舍内。
宿舍是间十来平方米的日本榻榻米式房间,屋内一桌一椅,加上季羡林的五六箱书,房间塞得满满的。想睡觉先要在门口脱鞋,坐在地毯上就地一滚就上床。但这二位自得其乐,他们情投意合,志同道合,或席地而坐,或抵足而眠,畅所欲言,常常今夜畅谈对国家未来开展的期盼和自己的前史使命。他俩后来都把这第一次会晤看作二人生死之交的开端。
无巧不成书。此刻臧的夫人郑曼也从南京来上海。她本来已在南京谋得一份作业,但不定心臧一人在上海,便辞掉作业来照料臧的日子。幸而上海武训校园已为来讲课的教师在山东会馆预订了几间客房,郑曼只好先去会馆寓居。不过后来郑曼了解季老的情况后对季很是尊重,新我国建立后季是臧家常客,传闻每次季到臧家,郑曼必亲身下厨,做几样家乡风味的鲁菜(郑曼自己是浙江人)。
季老性格内向,不喜结交朋友,只要臧一人在外。尔后五六十年中,虽然风风雨雨,每年春节二人必团聚一次,相互勉励,互述衷肠,直至生命最终时间。
不久季回北京当北大教授,臧则去上海武训校园当教师。武训校园已向会馆租借了几套客房(每户有一小院)供教师寓居。臧教师配偶、田仲济配偶、姚雪垠、孟秋江等都搬来了。我家住在会馆平房,离客房不远。传闻那么多位教师和同乡成为街坊,咱们一家人都喜不自禁。
其时陶行知先生也是4月离重庆到上海。他来前就已托付李世钊兴办上海武训校园(还得到郭沫若支撑和20万法币的捐助)。其时上海云集了一大批闻名文明人士,他们应邀来校教课。除臧克家外,还有田仲济、景德、孟秋江、姚雪垠、孙起孟、金中华、焦敏之等人。这些人们之所以欣然接受约请来校园讲课,首要是出于对孔孟、武训的崇仰和对陶行知的敬重(陶行知自称是“武训主义者”)。
1946年8月上海武训校园在上海山东会馆和齐鲁校园内正式开学,接收的学员首要是作业青年、小学教师,以及一些没时机进大学的失学青年。臧克家每周一次“诗词创造”课,每次两小时。我在齐鲁校园上初中时李世钊是我的语文教师,他见我喜好文史,就发动我去武训校园听课。好在校园是使用每天晚上和星期天上课,我就一边上高中,一边在武训校园听臧克家等几位教师的课,成为他们的学生。
1930年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(后改称山东大学),在语文考卷中写了28个字的杂感:人生永久追逐着幻光,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,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。这打动了闻一多,虽然臧的数学考零分,但仍破格选取他入学。
大学三年级时臧克家宣布第一部诗集《痕迹》(诗集中有一篇《老马》,为臧前期代表作)和第一部长诗《罪恶的黑手》,得到闻一多、茅盾等长辈的好评。抗战迸发后他去了大后方,在部队和当地做抗日宣传方面的作业。
抗战八年他一向比较烦闷,没时机宣布著作,经济上好像也不宽余。他和郑曼女士于1942年在重庆成婚时,传闻连一张像样的成婚照都没有。成婚照是1946年到上海后补照的,他将相片分赠给李士钊等老友(有些记者见相片背面有1946字样,误以为诗人是1946年成婚的)。
上海从1937年后成为孤岛,1941年又被沦亡。抗战成功后敌伪文明被肃清,上海文坛一片惨淡。广阔市民方枘圆凿是年轻人遍及感到精力空无,因而臧克家的诗词、姚雪垠等人的小说在上海大受欢迎。郭沫若称他们为其时烦闷的上海文坛打开了一扇窗。臧克家早年在青岛时期的著作,如《老马》《难民》等都在上海从头宣布,长诗《罪恶的黑手》及诗集《痕迹》也由上海书店从头刊印,蜚声上海诗坛。《文汇报》夸大地说:他“简直一夜之间成了天才诗人”。
臧克家到上海后还创造宣布了一批新的政治讽刺诗,极受上海市民欢迎。后来他将其间17首汇集成诗集《宝贝儿》,交由上海万叶书店出书。这17首诗中,最妇孺皆知的是《成功》和《宝贝儿》二首。前者说所谓“抗战成功”已成了大小官员抓取金钱、分配官位的代名词,而真正为国挂彩的兵士却手持“领奖”证明书沿街求乞。后一首则开门见山地呼吁公民不要听那些空泛哄人的文告和许诺。
1947年他又宣布了《生命的零度》。这首诗以“前日一天大雪,昨晚八百童尸”的一则本市新闻为体裁,指出八百儿童在劲风雪中,“像一支一支的温度表,/一点一点地下降,/总算降到了生命的零度!”但社会的反应简直是“零度”。全诗狗仗人势,为八百儿童亡灵鸣不平,对其时社会冲击很大。
臧教师其时刚四十开外,面庞消瘦,但精力飒爽,谈吐诙谐,振奋时好像连眉毛都含笑诙谐。他虽在大后方待了八年,但基本上仍操山东话,搀杂一些南边口音。他讲课时常常引经据典,妙语解颐,即便课间歇息时间,他也常给学生说个笑话,来段诙谐。
其时班上的学生大部分是上海人,小部分是山东人。他说上海话常使北方同学闹误解,比如上海人说“咱们都来作诗”,北方人听的是“咱们都来作死”,难免吓一跳。他还说上海话的一大特征是音平,有些上海诗人在诗中喜欢用“啊”以提高诗的热情,有的诗只要10来行,却用了10几个“啊”,朗读起来像乌鸦叫。这些话听得咱们捧腹大笑。
他又说山东话也有缺点。比如他有首抗战诗,内有一句“杀得敌人尸横遍野”,山东人念成“杀得电影鞋油纷飞”,这哪儿仍是诗!所以咱们要学习以北京话为根底的国语(注: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)。北京话“平、上、去、入”清楚,这才使诗有美感。臧教师便是这样耳濡目染地引导咱们喜好诗词,并使咱们认识到普通话对诗词的重要性。所以每次他讲课都济济一堂,慕名而来的还有上海几所大学喜好新诗的学生。
臧教师一开端就介绍闻一多创造的新诗、古诗代表作,叙说恩师终身寻求立异、变革、前进的故事。闻一多是我国闻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,不只宣布过多篇妇孺皆知的诗歌,并且是五四运动呈现新诗之后,第一个提出新诗也要改造的诗人。
为什么新诗也要改造呢?各位理解,1917年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上宣布白线首,算是新诗年代的开端。之后,我国文坛上曾呈现一大批精彩的新诗,如胡适的《测验集》,郭沫若的《女神》,闻一多的《死水》,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,周作人的《曩昔的生命》等,为广阔公民方枘圆凿青年所喜欢。但30年代后新诗也呈现新问题,首要是结构上过分随意,叙说上过分松懈,内容又往往是东一棒西一锤的无病,与人们的“脍炙人口”脱节。
闻一多早年受家庭影响拿手旧体诗,五四运动后受新文明运动影响摒弃旧诗改写新诗,是新诗的一个代表人物。但1928年虚怀若谷他的新诗名望鼎盛时期,忽而又转入对我国古典文学和旧诗词的深入研究。由于他发现中华文明宝库的博学多才,新诗和旧诗不只不对立,并且假如新诗能学习旧诗的格律方式,将极大地推进新诗开展。
1925年5月他在《诗隽》上宣布一篇重要文章《诗的格律》,提出新诗也应像旧诗那样寻求三美:一是音乐美,着重诗应有平仄,有韵脚,有音乐感。二是绘画美,着重辞藻的选择要秾丽、显着,有颜色感;每一句诗都能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画面。三是修建美,着重诗要“有节的匀称,有句的均齐”,就像一座规整修建物。要做到三美,就需要对旧诗有厚实的基本功。闻一多特别着重熟谙旧诗极大地丰厚了新诗的创造。他说“对旧诗体的深研反哺了我对新诗的创造”。
臧克家则以为,旧诗的三美首要体现在押韵,所以他提出“新诗的押韵观”,以为新诗首要要学习旧诗押韵的长处。他也附和恩师的观念:新诗要有成果,有必要先有厚实的古文和旧诗词的根底。
臧克家自幼受家庭影响也有极厚实的古典诗词根底。1930年他被青岛大学选取后,就表现出既在旧诗方面有深沉功底,又在新诗创造方面独具天才的特征。这正是闻一多想找的培育对象。
臧克家后来的创造路途也阐明,他和他的恩师相同,归于对旧诗旧文学有深沉功底和造就,而在新诗创造上大放异彩的诗人。
1946年7月闻一多被间谍暗算,对臧影响很大。他在《文汇报》上宣布了10多篇留念诗文。1946年的中秋节,上海交大的“闻一多诗社”建议大学生中秋节诗词歌咏晚会,臧教师应邀在会上做了《闻一多先生诗创造的艺术特征》的陈述(第二天刊登在文汇报上)。他在陈述最终热情地说:“在我的心上,站立着一些崇高的印象,它们给我鼓舞、给我日子斗争的勇气。有了它们,我的笑,才有含义;我的泪,才有光芒。有了它们,我的生命才不空无。在这些影子傍边,闻一多先生是至高至大的一个。可以说,没有闻一多先生,就没有我的今日。”
1946年12月5日是武训先生108周年诞辰。武训校园和上海文明界人士一起建议举办留念大会。12月5日下午2时,留念大会在上海山东会馆的大礼堂举办。到会贵宾有民盟中心委员刘王立明、老教育家邰爽秋等十余人,还有“不速之客”的孔祥熙,除此以外还有上海各大报纸记者、武训校园师生等共三百来人。大会主持人是李士钊。作者作为武训校园的学生被李校长抓公役,担任详细会务。武训校园教师中,臧克家在上海已有点名望,所以作为贵宾在台上“荣誉席”就座,其他教师就在下面前排的“特别席”就座。
众所周知,早在抗战期间,孔祥熙便是贪婪敛钱的模范。他大,遭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痛斥。不过其时孔还有他假装的一面,如自己出钱办校园、做慈善作业等。孔是山西人,但他自称山东血缘,是孔子75代孙。他宣传自己尊孔孟,崇拜武训,凡有关留念孔孟、武训的活动他每次必到,或不请自到。刘王立明和臧克家等人见他也到会十分不满。所以留念会简直变成了声讨会。
大会应孔祥熙的要求先请他做“特别讲演”。孔竭力宣传自己怎么舍财兴学,乐善好施,足足揄扬了一个多小时。接着贵宾们说话。其间民盟中心委员刘王立明的说话特别引人瞩目。刘在其时是位受人敬重的妇女运动首领。她于1920年从美国获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,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,担任国际妇女控制会副主席,并一向担任民盟的中心委员。1944年因在上海与陶行知等人一起建议建立保证委员会而闻名。她也是臧克家敬重的长辈。碰头时臧敬称她为恩师、刘先生,有时亲热地称为大姐。
刘王立明在那次大会上说话的粗心是:不管哪一种人,不论是有权有势张牙舞爪的达官贵人,或受冻挨饿的贫穷小民,他们都逃不了一个字——死。可是虽然“死”字,有的人虽死犹生,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。前者就如武训、陶行知等,他们永久活在人的心上。而后者便是现在那些贪官蠹役,他们搜刮民脂民膏,为富不仁;虽活着也仅仅死人。她这一席话锋芒直指孔祥熙等达官贵人,因而一再被火热掌声所打断。
这次大会在其时国统区发生不小影响。会后第二天在上海的多家中外报纸上都作了报导。文汇报的标题是:刘王立明等痛斥贪官蠹役为富不仁。在报导中特别说到刘王立明提的“有的人虽死犹生,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”。现在看来,刘王立明可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人以高度归纳的句子,总结两种人、两种人生观和两种人生归宿的人。她爱憎清楚,讴歌了永久活在人们心中的武训,抨击了虽生犹死的孔祥熙之流。
臧克家有篇成名作叫《有的人》。全国中小学学生都能背诵它。臧克家称这是他1949年为留念鲁迅去世十三周年而写的一首抒情诗。但一些知情的学者(包含臧的密友李士钊)以为,这首诗显着是他在1946年那次大会上受刘王立明说话的启示而作的(有其时报纸为证)。
惋惜的是,当事人从没有揭露表态。所幸刘王立明为人宽宏大量,没有计较此事,还一向有意培育臧为民盟作业的接班人。她于1951年介绍臧克家参与民盟。后来国内政治运动不断,而刘王立明命运多舛。据李士钊教师生前告我,1978年11月26日一些山东文明界人士在北京臧克家寓所集会,追思他们在山东省一师的恩师王祝晨时,李当面告臧关于刘王这一些情况,臧听后潸然泪下,并说我愧对我的恩师!
臧克家见自己最爱戴的陶行知、闻一多、刘王立明等都是民盟盟员,因而对民盟十分信赖。武训校园停办后,臧克家积极参与民盟安排的反蒋,因而上了间谍的黑名单。1948年末他在民盟安排下脱离上海潜去香港暂住。直到1949年他应邀来北京参与开国大典,后来就一向留在北京作业。1957年他因宣布“毛主席诗词解说”而到达作业巅峰。
臧克家在武训校园期间尊陶行知为恩师。陶行知在生命的最终100天,在上海屡次宣讲他的教育思维和理念,臧克家简直每场必到,并认真听讲,谦虚发问,得到陶行知的称誉。
晚年臧教师曾对李士钊说,最使他感动的校歌是陶行知为武训校园写的《武训颂》,由于它爱情真诚,朴素无华,他已把它搜集在《臧克家全集》中。最赏识的修建是上海山东会馆,由于那里有校园、操场、礼堂,有孔孟和武训的祭坛和业绩展览室,还有明清风格的楼台亭阁。陶先生说它最适合做少年儿童教育的基地。
传闻晚年的臧克家曾计划去南京仰视陶行知墓,并去上海山东会馆遗址访旧,但因健康原因没能成行。不过他曾屡次去聊城武训新居观赏。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他应邀参与武训留念堂落成典礼,当场作诗一首,以表他对一代圣丐的敬仰之情。诗云:“破钵百衲度春秋,心铁情痴为众谋。今古完人究多少,何于一丐作苛求。”这首诗或许是诗人最终的绝唱了。供图/郭衍莹